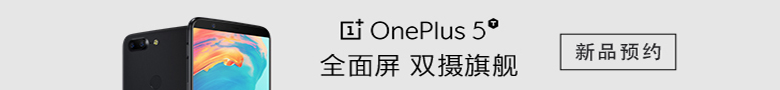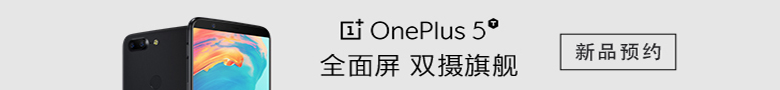留念梁思永先生,他为我国考古学而生
留念梁思永先生,他为我国考古学而生

梁思永(左)和哥哥梁思成在西北冈开掘工地合影
本期,咱们给咱们讲一个伟大的我国学者的故事。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讨院召开了一次气氛火热的欢迎茶会,以庆祝上一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开掘取得的丰硕成果。这是我国人领导和组织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开掘。会上,此次开掘负责人李济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先生在讲演中说,他们二人搞考古都是半路出家,真实专门研讨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
他们在等候着我国第一位科班出身的考古学者学成归国。他便是梁思永。
得知人们对儿子的等候,梁启超又快乐又惊慌
1920时代曾经,现代考古学于我国而言,仍是一个没有落地生根的西洋学科。梁思永之所以选择如此冷门的专业,与他的父亲有关。他是梁启超先生的次子。梁启超,这位我国近代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和思维家,也极力推进考古学在我国大地上生根发芽。
20世纪初,梁启超即编撰文章介绍丹麦古物学家汤姆森闻名的三期论。汤姆森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三期来描述欧洲史前史。该学说在19世纪60时代得到广泛传播,至今仍然用于世界各地的史前考古学。梁启超因而倡议依此学说,来编撰我国史前史,而非神话传说,“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我国史前之史,绝不为过。”沈颂金在《梁氏父子与我国近代考古学的树立和开展》一文中如此说。
梁启超还担任其时的我国考古学会会长一职,大力支持郊野考古作业。1926年,李济赴山西西阴村考古开掘时,梁启超曾两次给主政山西的阎锡山写信,请他对这一新式科学事业予以支持。在那个时局动荡的时代,李济的考古作业因而得以顺畅打开。
1926年10月,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古斯塔夫拜访我国。梁启超参加了10月22日举行的欢迎会,并作了题为《我国考古学之曩昔及将来》的闻名讲演。他在讲演中回顾了我国考古学之前身——金石学的成果,一同还极具前瞻性地展望了我国考古学的开展:他以为我国考古学既要有意识地加强郊野考古开掘,又要发起先进办法和人才培养。他相信“以我国当地这样大,前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厚,尽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
“梁启超是把近代西方学术介绍到我国的传播者,是我国近代‘新史学’思维的创始人。他发起运用多种材料研讨史学,其间包含考古学材料。在我国考古学正式诞生之前,他就现已为考古学的传入做了许多铺垫作业。”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讨所所长陈星灿如是说。
梁启超将交融了西方考古学理念的新史学思维传播到我国,一同也指导自己的孩子成为实践这一理念的先行者。九个子女中,梁启超期望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学,所以送他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因而,在1927年欢迎李济从山西考古归来的茶话会上,当他听到两位走在我国考古学最前沿的人自称“半路出家”,并说梁思永才是“真实专门研讨考古学的人”时,其心里应是非常激动与快乐的。当天晚上,他就给梁思永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我听了替你快乐,又替你惊慌,你将来怎么才干当得起‘我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是非常尽力才好。”
梁思永没有孤负父亲的期望。他正尽力积聚力气,预备将其转化为我国考古学“大厦”之坚固基石。
从最高学术殿堂到极寒东北郊野
1904年,梁思永生于上海,后随父亲流亡日本,就读于神户市华侨所办的同文学校。1913年,他随家人回国,不久后入读其时北平西城的崇德中学。1916年至1924年,他就读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在这八年间,梁思永学习勤奋,成果优异,他与兄长梁思成合作翻译英国学者威尔斯所著的《世界史纲》,并在梁启超校订后出书。在此期间,他也参加了五四学生运动,“为自己的勇敢行为感到非常自豪,并把他被关时所吃的干馒头带回来给家人看,以示其爱国之心。”
1924年夏日,梁思永毕业,次年赴美留学。梁思永在哈佛大学研讨院专攻考古学和人类学,曾参加美洲原住民古代遗址的开掘,专门研讨过东亚考古学。学习期间,他经常与父亲通信,讨论学业和回国实习事宜,得到了父亲的大力支持。
1927年7月至1928年8月,为了解国内考古状况,梁思永曾回国在清华国学研讨院担任助教,收拾了李济先生在西阴村开掘的陶片,后来写成专刊出书。学习期间他还编撰《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一文,对东亚考古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见地。
1930年夏,梁思永毕业归国。回国后,梁思永就参加了刚建立两年的中央研讨院前史语言研讨所考古组(以下简称“史语所考古组”)。同年秋,他开端履行该所发起的“东北考古计划”——赴黑龙江开掘昂昂溪遗址。深秋入冬时节,他又从通辽转入热河进行考古查询。陈星灿曾在文章中写道:“他和搭档在极点艰苦的条件下,行程过千里,历时38天,完结了我国人第一次体系的东北考古查询。”
这里的艰苦,有社会和天然环境两重因素。“其时的东北考古,控制在日本人和俄国人手中。梁思永只带着帮手,深化东北考察,是冒着巨大危险的。”陈星灿解说说。
在热河,梁思永见到的是社会动荡下人迹罕至的村落和田地。他在查询陈述中写道:“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咱们精力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当地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止,白天时刻的缩短,咱们的行走止息彻底受了环境的分配,没有一点点的自在。”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亲身冒险收集考古材料,是以往我国文人知识分子不屑去做的,梁思永和我国新生代的考古学家去做了。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期用内涵丰厚的考古材料来重修古史。
陈星灿以为:“梁思永此次的考古查询,让咱们对东北的史前文明有了第一次逼真的认识。特别昂昂溪遗址的史前渔猎考古材料,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从此,梁思永的考古作业开端为我国考古学带来簇新样貌。
发现“后冈三叠层”,开掘山东城子崖
回到北平后,梁思永完结了黑龙江昂昂溪的开掘陈述,于1931年春,参加河南安阳小屯及后冈的开掘。此次开掘,是史语所考古组在安阳殷墟的第四次开掘。第一次由出身河南本土的甲骨学家董作宾主持,第二、三次则由史语所考古组新任组长、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我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李济先生主持。
此次开掘,史语所考古组调动了悉数力气,包含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等人,考古规划和人员数量均空前庞大。这其间,最关键的力气是梁思永的参加。自从梁思永参加之后,殷墟开掘才逐渐走上科学的轨道。
此次开掘持续了50余天,因时局动荡而暂停。梁思永所以带领团队转到山东城子崖进行开掘。
1931年深秋,梁思永回到安阳,进行第五次开掘作业。这一次他发现了闻名的“后冈三叠层”——即小屯(商)、龙山、仰韶这三个时期的文明层有非常明晰的叠压联系。“这一发现在其时有限的考古开掘材料中,就现已可弄清仰韶文明、龙山文明和商文明的相对时代联系。”陈星灿点评这一发现时说,“跟着50时代后期,仰韶文明和龙山文明之间的过渡层——庙底沟二期文明被发现,才终究确定仰韶-龙山-商文明的开展序列。”
而梁思永之所以能识别出这样的地层联系,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区分地层,而非单纯以深度来区分,这与其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地层学办法联系密切。梁思永曾跟从研讨美洲考古的祁德去过美国西南部,参加原住民遗址的开掘。其时,祁德要求依照地层的天然改变来区分地层。因而,梁思永将这种新办法应用于国内的考古开掘。这也令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考古地层学的奠基人。
梁思永之所以在第四次安阳开掘后转到山东城子崖进行开掘,一方面由于河南战事所迫,另一方面也由于在城子崖已有重要发现——龙山文明。
有关龙山文明,梁思永在其文章《龙山文明——我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中介绍了它的由来:“龙山文明之存在的依据,最初是吴金鼎在1928年春间所发现而提出的。在当地叫做城子崖的台地的西面断崖上,暴露着一个完好的文明层。在这里这位发现者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儿带黑色光泽的陶片。被这个文明遗物部分地堆成的城子崖,是在山东省历城县东七十五华里的一条小河的东岸上,正对着小小的龙山镇。因而,龙山这个姓名就作了所发现的文明的称谓。”
吴金鼎的发现并非偶尔。这是李济等学者对山东考古的注重使然。他们依据文献记载和已有的考古发现,以为沿渤海、黄海的省份在考古学上有重要位置,所以赴山东开展考古查询。开掘城子崖的意图,既是为了研讨我国文明的源头,追溯商朝前期及曾经的遗存,也要探查东部比殷墟更早的遗址,为批驳其时盛行的“我国文明西来说”增加依据。
1930年底,李济、董作宾、吴金鼎等人对城子崖进行了第一次挖掘,发现了龙山黑陶期的围墙、陶窑,还获得了陶片、骨、石器等标本。到了1931年秋,梁思永主持了城子崖遗址的第2次开掘。在开掘中,他依据地层学办法区分地层,发现了灰陶文明和黑陶文明两个叠压的文明层;在开掘作业的组织上,他改进了办法,提高了功率;一同,他也在后续研讨中对文物进行了类型学剖析,为我国考古类型学奠定了根底。
后来梁思永主编了《城子崖》陈述的编写。这本陈述中,他自己编撰了几章,还对悉数稿件进行了详细审理和修改。这是第一部由我国考古学家自己编写的郊野开掘陈述,创始了郊野陈述的底子编制。其间包含“标准的考古底子概念和术语,更重要的是一套完好的文字和图片表述体系”。这种编制至今仍被沿用。
“依据龙山文明的考古发现,梁思永先生第一次体系总结了这个文明的特征,并作了分区的尝试。”15虽然由于其时考古发现的局限,梁思永对龙山与仰韶文明的联系问题上,没有超出龙山文明向西开展、仰韶文明向东开展的“东西二元敌对”假说的领域,但陈星灿以为,“他对仰韶、龙山与殷墟商文明的辨识是适当精确的。”并且“龙山文明是我国文明前身的解说,确在适当程度上不坚定了其时已盛行了十多年的‘我国文明西来说’,这也是梁思永先生的一大贡献。”
“拼命三郎”与西北冈开掘
了解梁思永的人都知道,他有着“拼命三郎”的作业精力。1931年春刚结婚三个月,梁思永即参加在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开掘,之后便总是出现在考古现场。他的女儿梁柏有曾撰文说:“他在野外作业中和工人们一同挖掘,虽然条件非常艰苦,有时需求卷起裤腿在水中泡上几个小时,为了作业不受雨季影响,有时还要挑灯夜战,吃饭也无定时,作业紧张使他无法脱离工地,只得啃点白馒头,喝几口凉水算作一顿饭,但他仍是干劲十足。”
在艰苦条件下如此拼命作业,毅力再强,身体也吃不消。1932年春,梁思永刚28岁就患上了烈性肋膜炎,因而卧病两年。医生从他的肺中抽出了四瓶如啤酒颜色的积水。
1934年春,他的身体刚有所康复,便着手完结热河查询陈述。同年秋季至1935年,又赴安阳主持了三次殷墟侯家庄西北冈殷王陵的开掘,也是殷墟考古的第十至十二次开掘。这三次开掘的收获和规划,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峰。特别在1935年秋的西北冈第三次开掘中,每天招聘500名工人,这是到那时为止我国郊野考古史上雇人最多的。开掘面积达9600平方米。这三次开掘揭开了1232座殷商墓葬,其间包含10座大墓。
曾跟从梁思永参加西北冈开掘的夏鼐先生在留念文章中这样写道:“梁先生那时刚过三十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好久,瘦长的身段,苍白的脸色,显得身体还没有彻底康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是像生龙活虎一般地到处奔跑巡视,他的那种忘我的作业精力,使他彻底忘记了身体的软弱。”
“西北冈的大规划开掘,充分展现了梁思永先生卓越的考古专业才干以及超卓的管理能力。其时时局不稳,人员又多,他作为开掘主持人,既要保证开掘的有序进行,又要组织几百人的行动。即使今天看来,其时的开掘场面也很壮观,很了不得。”陈星灿点评说。
西北冈大墓的开掘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重。西方汉学家和日本学者纷纷发表文章,讨论商代社会和文明。当史语所创办者傅斯年陪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拜访开掘现场时,他们和梁思永一同坐在大墓工地上,望着殷商的遗迹,留下了一张合影,定格了那一前史瞬间。
他没有孤负父亲的期望
开掘西北冈后,梁思永本计划好好审视一下这些非凡的出土物,写完开掘陈述,再组织下一步的开掘作业。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迸发,计划被打断。他便跟从史语所考古组和珍贵文物曲折各地。先到长沙,后经桂林到昆明,之后又搬到“地图上找不到的”位于四川的偏僻村庄——李庄。这期间,日子艰苦,物资紧缺,搭档们个个面有菜色,况且身体虚弱的梁思永。
1942年,梁思永肺结核剧烈发生,一度病况危殆。1944年春节,他曾趁着夫人不在身边,悄然问主治医生:“我有一件事向你商议,看来我这身体是无法彻底康复康健了。但是现下我仍可牵强作业。我想要知道我这病体能不能牵强支持作业一年。只要给我一年的工夫,我便可将西北冈的陈述赶完了。那时纵使因精力耗尽而去世,我也是甘心的。”也许上天为之动容,将一乘了一个十。
梁思永将西北冈王陵的材料收拾出多达241页的手稿,还包含一个初拟的分章目录。写作这些手稿,梁思永真可谓呕心沥血。陈星灿解说说,这些手稿是在多种困难状况下写出来的:一是梁思永的身体状况差;二是日子条件艰苦;三是没有研讨的条件。做研讨作业的人知道,研讨考古材料,最好是摊开,以方便观摩、记录和测绘。但其时的器物和材料底子没有当地摊开。梁思永只能将材料从箱子里翻出来,收拾完之后再放回去。大量材料便是在这种拿出来、放进去的繁琐程序中诞生的。陈星灿在说到这些细节时,不由感慨“非常感动”。
1945年抗战胜利,梁思永到重庆做了一次大手术,截去了几根肋骨,以便让感染结核的左肺萎缩下来,之后便回北京保养身体。1948年,他因在考古学上的突出贡献而当选中央研讨院首届院士。1949年,国共内战局势逐渐明朗,国民党政府败退至台湾,也将史语所考古组的材料一并带去。梁思永编撰的手稿,也成为考古组的珍贵材料,一同去了台湾,等候有心人的体系收拾出书。
不过梁思永留在了北京,参加了1950年建立的考古研讨所,并担任副所长。此时,他不管懦弱的身体,仍尽心计划和指导郊野开掘和室内研讨作业,一同不忘积极扶持青年考古学者的生长。
1954年2月,入院检查的他本计划如无大碍就回所持续作业,然而他却再未能走出医院大门。4月2日,梁思永心脏病发生,告别人世,享年尚不满50岁。临终前,他对家人说:“我不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咱们永别了。”
梁思永先生的奋斗停止了。他时间短的一生是为我国考古学而生的。他没有孤负父亲的期望,为我国考古学贡献了自己悉数的智慧和汗水,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星灿说:“梁思永为我国考古学注入新的办法,奠定了类型学和地层学的根底,树立了考古开掘陈述的写作典范。他是殷墟前期的开掘者之一,是商文明的重要发现者。他是我国考古学的奠基人。”
李济说:“梁思永先生,我国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现已把他悉数的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
夏鼐说:“他的汗水现已耗尽,脑汁现已绞干,现在连他的尸骨也已成灰,但是他的精力和功劳是永存永存的。”
斯人已逝,余波荡漾。1954年夏,梁思永去世的音讯传到海峡彼岸。他曾经的搭档和学生,怀着哀悼之心,决定做一件事——全力以赴完结梁思永生前最挂念的西北冈墓葬开掘陈述。董作宾与李济商议后,决定由高去寻对照实物材料,辑补梁思永之遗稿。李济将写有22万字的遗稿亲身交到高去寻手上。从此,这位在古文字学、史学、民俗学和古器物学上都颇有造就的学者开端将余生精力都放在这一件事上。从收拾遗物、核对、测量、照相再到体系收拾材料,他几乎从头编写了陈述;历经十多年的日日夜夜,高去寻总算完结了以《侯家庄》为名的七本系列陈述。陈述扉页上这样写着:“梁思永未完稿/高去寻辑补。”这“辑补”二字,从未饱含如此情意,从未载有如此分量……
称谢:感谢我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讨所所长陈星灿对本文的大力支持和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南京大学前史学院张良仁教授和美国史密森博物学院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刘嫄博士对本文的细心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