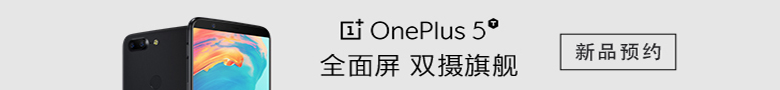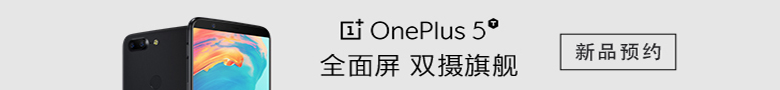历史学家徐国琦:太强调不同
“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同对方打交道的时候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天真和无知。”在《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一书中,香港大学历史学特聘讲座教授徐国琦这样写道。他看到,虽然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可是,人们常常把目光聚焦在过去存在的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对抗当中。
中美历史中的共有时刻对双方而言包含着截然不同的含义。美国人自以为美国的使命是“改变中国”,而中国人则常常把这段历史看作是包括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种族主义和饱含屈辱的百年国耻。徐国琦在这本书中,梳理了中国派往世界的第一位使节蒲安臣、19世纪清代留美幼童、美国第一位汉语教师戈鲲化、中国的美国顾问古德诺、“洋孔子”兼文化大使约翰·杜威、国际体育等六个案例,试图从“共有的历史”来寻找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跨越冲突进行的合作、克服隔阂开启的对话渠道,并以此推动人们朝这个方向努力。在他看来,消极的历史观对国家的未来没有好处,过于强调领导人的作用也并不可取,未来人类的历史将会越来越共有,指出这一点,是历史学家应尽的责任。

徐国琦1962年出生于安徽省枞阳县下桥村,先后在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1990年,他进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主要导师为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入江昭的带头之下,历史学界开始强调国际史的重要性,要求打破民族国家界限,强调文化、非权力因素的影响。徐国琦的“国际史三部曲”:《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战中的华工》就是从三个不同的题目研究国际史。在此基础之上,徐国琦又提出了 “一切历史都是共有的历史”的观点,着眼于共同的历程及追求,侧重文化范畴,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作用。
“没有一个历史观是万能的。”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徐国琦表示,“共有历史的视野、关怀、适用性比目前所有的历史方法更有意义,它可以整合历史研究。可以研究性别史、文化史、大众文化。过去,我们太把历史碎片化,太强调不同了,政策决策、商业决策都会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冲突对抗蒙蔽,共有的历史强调求同存异。”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立新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同国家之间的经历常常有很多交叉重叠之处,研究不同国家间的“共有的历史”对构建稳定、和平的国际关系是有意义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则看到,国内学者的概念化能力相对薄弱,他认为徐国琦有宏大的对历史的观照,还能够用扎实的档案研究带来的新的材料和丰富的细节。
徐国琦认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得益于他的“边缘人心态”。他告诉界面文化,2019年是他离开中国大陆的第29年,意味着他在海外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他在大陆生活的时间,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边缘人”。而且,作为一位研究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的学者,他必须“两脚踩东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做“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伦不类”的学问。另外,他还指出,历史学家应该“出世”,不对任何人、任何政党负责任,只对自己的学问和题目负责任。

界面文化:长期以来,中国人的近代史书写有一种“创伤叙事”,把这段历史看做是屈辱的历史。你怎样看待这种历史叙事?
徐国琦:中国的“创伤叙事”不科学,也不自信。中国除了鸦片战争以来受到的列强凌辱,还有其他值得一说的事情。比如,在一战问题上,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尽管没有在短期内收回山东,但也参与创造了国际秩序。我们有14万华工在法兰西、比利时工作,自发、有组织地参与拯救西方文明。洋人说他们是“苦力”,一百年来都没有承认他们的贡献,直到最近才被迫承认。这段历史不是中国的耻辱。如果按照这种“创伤叙事”:德意志帝国是在对法国的羞辱中建立起来的,法德应当不共戴天;日本是唯一一个被核武器攻击的国家,日本应该和美国势不两立;又例如美国,内战打完又是一家人,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虽然还有无数的问题,黑人还受到歧视,但美国还是在抚平创伤。而我们,却整天要把伤口揭开。
中国“创伤叙事”的最大问题是造成了中国概念的不连续,我们把清朝当做一个中国,把中华民国当做一个中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当做一个中国,好像三者不关联。我“共有的历史三部曲”的最后一本《中国的概念》(Idea of China)当中,中国的概念(idea)是单数,不是复数。
总之,不自信的、片面的、消极的历史观对国家的未来没有好处。我们整天谈过去,把中国本身的历史叙事割裂、碎片化,因此到今天我们还在民族叙事里打圈,在边疆问题、两岸关系、香港问题上跳不出来。这是历史学者没有尽责。

界面文化:共有历史对中美双方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你也看到,对于这段共有的历史,美国人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提升中国。
徐国琦:中美两国人民有很多共同之处,都自命不凡,都持例外论观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立新写过一本《踌躇的霸权》,他指出,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不是情愿的。美国原本不想参与欧洲国际秩序,一战当中美国人原本中立,到了二战美国才意识到再不做霸主可能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人也是这样,过去认为自己是“天朝”,和其他国家不往来,到1901年才有外交部。
美国立国之后认为自己创造了独特的政体、独特的文明,可以拯救全世界。其实,历史是盘根错节的。有的美国人到中国来“拯救”中国文明,最后被中国人给“开化”了。例如,杜威刚开始到中国来一无所知,但他参与了五四运动。他影响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影响了他。
界面文化:除了双方对共有历史的认识有差别以外,你还指出我们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个误区就是太强调领导人的作用。
徐国琦:中国儒家文明强调“君子”的重要性,长期以来,我们太强调当权者了。人们说,尼克松是中国人的老朋友、基辛格是中国人的老朋友,我反而认为真正的中国人的老朋友可能就是蒲安臣。“老朋友”论太强调政治、经济、外交,却忽视了民间和文化层面的交流。而且美国三权分立,总统说的话常常无法兑现。另外,领导人是可以更替的,唯一不太常变的是深层的文化或者文明。所以我说,实际上左右中美未来的是平民百姓,是社会民间以及文化层面。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非常注重文化层面的交流。你认为,虽然现在看起来中美关系是经济贸易问题主导,但是这两个问题不久前还不是两国关系中真正重要的因素。过去真正重要的因素是文化吗?
徐国琦:经济问题到1979年北京和华盛顿建交以前都不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经济上一落千丈,而且,美国到一战为止奉行文化国际主义,外交上不太愿意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中美关系长期以来更加侧重文化或者文明交流。从1784年第一艘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中国到1978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都非常小,对美国来说无足轻重。在1949年之前,虽然美国烟草公司、洛克菲勒的石油在中国的发展一枝独秀,但真正把中美两国联系起来的还是文化,是文明。
在1979年到1989年,中美贸易经济还不是重要的。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国际形势把中美两国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美国人需要中国,中国人需要美国,其中共同的纽带是前苏联。1989年之后,冷战结束,到1991年苏联不复存在,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又开始变化。中国成为贸易大国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经济贸易成为了中美主要问题。但是,经济贸易不过是表面,深层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全球大国冲突对抗的问题,因为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有潜在可能去挑战它。
界面文化:“共有的历史”听起来是非常积极的概念,不是注重两国差异和冲突,而是强调那些个案当中包含的积极方面。这里面也会包括负面的内容吗?
徐国琦:之所以不叫“共享”而叫“共有”,是因为不仅有正面,也有负面,这些历史都是共有的。在21世纪的世界,大家看到英国脱欧、法国黄背心运动、中美贸易战等等现象,但是共有历史的价值会越来越明显。作为人类共同体,我们都在一条船上。例如,有了核武器,人类才享有了长期的和平。例如环境问题,就像毛泽东写的诗句所说的“环球同此凉热”,全世界共同面对全球变暖的问题。又例如病毒问题,在冷战时代美苏不共戴天,可是美苏科学家依然可以联手消灭天花。在今天,恐怖分子已经能够跨越国界,他们和民族国家没有关系了,一个非洲的恐怖主义者也可以用脸书,用微信……这些都是共有的历史,未来我们的历史将会越来越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