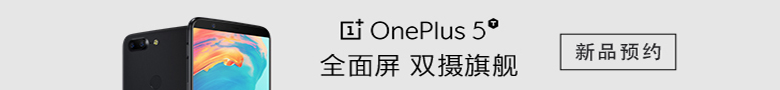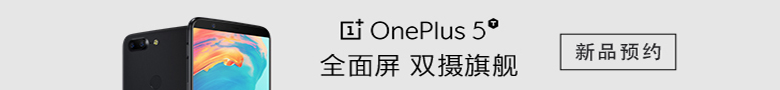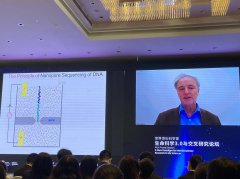隋末任侠的武力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隋末任侠的武力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任侠在地方乡里的势力中具有突出的武装力量性质。这种武装力量在隋末社会如何获得并维持自身的位置,与其他具有相似性质的力量之间有何区别与互动,都对于乡里秩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隋末时期的政治情况在杨玄感起义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民变中心的河北地区为代表出现了大量的流贼,这些流贼的领袖往往也是郡县勇力之辈其中也不乏任侠出身者,如“阿舅贼”刘霸道以及郡县长吏出身的翟让和同郡豪侠单雄信,这些人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往以本乡为核心小范围流动。
从成分上来看,这些武装力量与任侠组织十分相似,乡里的豪勇少年和有武名的轻侠是其中重要的力量。那么成分上颇多相似的任侠与流贼的区别何在?

一、任侠组织与流寇的不同
1.策略导向上,任侠组织和盗贼流寇有着根本的不同
隋末流寇的产生与长期存在大致有赖于三方面原因,其一是隋帝国连续性的军事行动及伴随的苛政,其二是隋帝国对于平叛的轻视和策略失当。
炀帝在平定杨玄感之变后,并没有认识到民变的重要性,而是继续进行对辽东的征伐,隋军主力聚集于辽东,各地的平叛只能依靠地方长吏和府兵,隋帝国逐渐失去对于全国的控制力。
其三是河北山东地区的频繁动荡,隋帝国对于河北与山东地区的控制力本就不如关中地区,战事的频繁和失去中央统一支持的郡县催生了大量的流民。流寇武装的建立动机多数不是推翻官府,而是团结求生。
在求生的需求之下,这些首领联合党羽和失去生活来源的流民结成了流寇武装。流民武装缺乏生活来源和军事训练,掠取人口和粮食以壮大队伍是其唯一出路。相比之下,任侠组织是一种需要寻求社会认可的精英武装群体。
相比于临时拼凑、随时变化的流寇,任侠组织具有相对稳定的关系和比较成熟的组织与规则体系。侠魁与好侠者,本身也都希望保护其资产与地位。
从任侠的特性出发,侠名本位是任侠体系的基础,而侠名的博取虽然不一定符合律令,但必须符合地方乡里的现实利益。从这一点看,维持地方的稳定是任侠组织的根本导向。

2.在活动方式上,流寇武装求生的主要手段就是劫掠
通过劫掠,一方面可以获得生存需要的物资,另一方面可以制造新的混乱,并利用混乱催生并裹挟更多的流民进行扩张。这种扩张使得战斗力低下的流民武装在与精锐的官军作战时更能博取有利态势。
流动则是流寇的另外一个特性,流寇的劫掠行动使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占据稳定的根据地。因而,流寇武装往往辗转州郡进行一定范围的流动作战,长白山贼孟让起于青齐地区,在加入李密集团前,孟让所部已经流动到江淮一代。基本由豪强构成的瓦岗军,在起兵之初也必须依靠流动劫掠。
徐世勣建议“东郡于公与绩皆为乡里,人多相识,不宜侵掠。荥阳、梁郡,汴水所经,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资。让然之,引众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聚徒至万余人”。可以看出流动作战与劫掠本身即密不可分。
与之相反的,任侠组织中,侠魁和资助的好侠者在乡里社会中占有大量的资源,很少会脱离乡里。豪强领导的瓦岗军拒绝在东郡本土进行劫掠的动机也是不希望损失翟让等人在乡里本土的声望。
与之伴随的,立足于本土的任侠组织需要以武力保证乡里的安全稳定进而保护自身的财产资源。许多任侠领袖都有对抗流寇叛乱的经历。如刘武周以平叛军功为官,薛举为校尉“雄于边朔”,受命讨捕,尉迟恭本人率乡曲讨捕山贼都属于任侠守土的情况。

3.在组织方式上,任侠比之流寇是更为稳定和严密的
不同的任侠群体依靠侠名和人身依附的关系构成了相互间有着紧密联系的树状结构。侠名、财力的大小以及武勇声望的高低决定着不同任侠个体乃至不同团体之间的地位甚至从属关系。
每一个任侠个体自身财力、侠名的变化都会带来个人在乡里权力的体系中的位置变化。从这一角度看,实力至上的任侠群体中稳定且明晰地晋升路线。除去少数对旧秩序极度不满或迫于生命威胁的人物外,与公权力相结合,保护和利用乡里根基是任侠主要的生存方式。
流寇则完全不同,流贼武装往往呈现一头或寡头的复杂结构,流民猬集在领袖之下,呈现杂乱无章的同伙关系。除去瓦岗军、窦建德军等少数有所纲领的集团,大部分农民军受困于补给和流动而无法保证稳定的群体。
在补给方面,流贼的抢掠完全是自发性的,呈现“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的自然状态。同时,其队伍规模也十分不稳定,连续劫掠成功往往裹挟流民,规模膨胀,而一旦补给不足或遭遇战败则大部溃散。
这种极为不稳定的情况导致流寇武装没有稳定的组织和升迁渠道。因此,追求利益的火并和离散在流寇中时常发生。

任侠群体较之同样是私人武力的流寇,虽然在人员成分和法度上可能存在相近之处,但根本上,任侠保留着以武名实力晋升为豪强、官员的晋升体系。
对于他们而言,保证乡里秩序的稳定和保护自身实力根基是比对抗公权更为有利的选择。笔者认为,不应当以善恶或者违反律令与否来同化任侠与盗贼,任侠集团本质上是私人武装,其所崇尚的侠名武力的评价体系,并不以朝廷法律为第一要素。
故而刘弘基盗马吹牛,牛进达曾穿箭为盗仍然不妨碍他们成为地方侠名的代表。从组织而言,任侠是带有隐秘性的小而精的团体,具有严密的组织,依靠于乡里的根基。
尤其在中央权力严重衰落的隋末,在更为独立和自由的立场上与郡县公权进行妥协甚至合作是这一时期任侠最为突出的特征。
二、任侠在隋末的作用
在隋末的政治情况下,许多地方往往缺乏官方军队自保,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任侠。这些任侠武装一定程度上与官方军队站在同一立场上,即保境安民,驱讨贼寇,但二者也存在相当差别。正规军队拥有严格的职务和配属体系,这是个人的勇武和名望无法替代的。
如大业十二年的张须陀部,在大海寺战败后余部分别由骁将秦琼和罗士信分领,但二人并不能独立成为军队的领袖,而是投奔继任的裴仁基。在张须陀军中尤以罗士信、秦琼为勇武亲信,罗士信“凡战,须陀先登,士信副将,以为常”。

但即使拥有如此亲信的关系和勇武声望,二人也只能对败兵进行临时性统御。空降而来的裴仁基却能凭借隋朝廷任命迅速得到各级兵将的认可,其中固然有裴仁基的个人能力,但也说明在正规军队中,来自朝廷任命的官职统属具有绝对的权威。
金城薛举是依靠县令郝瑗的任命和支持才能领兵讨捕,也从侧面说明军队的权威来自于完善的上下级关系和王朝政府的政治公信力,一旦公信力不再,军事统属就会瓦解。
任侠武装则与此不同,首先,任侠武装由于给养来自私人,所以规模并不大。如程知节不过“聚徒数百”尉迟敬德军事化的私人武装也不过“百骑”。
其次,任侠组织是由侠魁依靠个人能力和威望组织起的私人武装,带有深刻的私人性。其中有如程知节、尉迟敬德部下这样带有军事化特点的组织,也有王君阔、王君愕兄弟和牛进达等带有劫掠和流寇性质的团伙。可以说这些人物的身份都是任侠,但他们的组织性质和后续发展都受到了其个人性格的影响。
最后,大部分任侠团体只是通过物质和恩义相互连接。许多个体的任侠并不常聚一处,交往关系也较为松散。任侠群体中虽有高低之别,但相互依附的关系往往基于恩义和个人意愿,“合则从,不和则去”的情况颇多。
如刘黑闼为轻侠“与窦建德相友善”,但在其起兵之后,却是“从郝孝德为群盗,后归李密为裨将”。说明私人关系并不一定能转化为明确的从属关系。侠魁与轻侠之间分合多有自主,与基于兵役的军队体系完全不同。

大业末年多有任侠或主动或被迫从军。如早年“侠气飚腾,轻百金而有裕”的尉迟敬德“大业末,从军于高阳,讨捕群贼,以武勇称,累授朝散大夫”。尉迟敬德得军功之后只是被授散官。这种情况在《旧唐书·刘武周传》和洛阳地区出土的应募兵将《卞鉴墓志》和《王弘墓志》中也可以印证,刘武周“募征辽东,以军功授建节校尉”。
卞鉴“枭感充斥,以勋授奉诚尉”、王弘应征暂摄城守,“酬庸命爵,荣典乃加,诏授奉诚尉”。说明大业末年来自隋帝国中央的募兵,往往战时结束即加遣散,其酬劳也多是加封散官。但这样的酬庸在任侠回归乡里后往往转化为个人名望。
这也使他们在地方官府的互动上有了极大的主动权。地方侠魁除保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外,往往也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官方的军事序列中。
从职权来看,地方侠魁充任的多是府兵长官。府兵序列在地方权力体系中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大业末年的地方政治中,府兵与守令之间往往存在着互动关系。从制度层面看,守令的行政权力往往在职权上可以支配地方军事。
如名将张须陀以齐郡通守为讨捕大使,李渊以卫尉少卿镇弘化郡军事、杨义臣以赵郡守平向海公,都是强力郡守支配地方军事的典型。作为军官的刘武周、薛举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本郡守令的下属。

但从另一方面看,府兵军官和郡县长官往往在现实存在相互掣肘,李渊为太原留守,武贲郎将高君雅命为副手实为监视。这种情况在侠魁为将的州郡更为多见,如刘武周虽为太守王仁恭亲将,却散布谣言,树立私人威信,薛举则是取金城令郝瑗代之。
刘武周、薛举作为地方侠魁的领袖在反对长吏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阻力,说明在形式的从属关系下,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地方长官。这种巨大影响力主要来源于他们个人的武名和巨大人脉所牵涉的私人武装。
总结
在武威郡面临薛举的军事威胁时,首先被地方豪强拥戴的并非理论上权力最大的郡守而是地区的任侠武装领袖李轨。这充分说明任侠在地方虽然需要公权名位,但已经以其武力超脱了公权的管制。
兼具侠魁与武官双重身份的人物与一般的府兵军官、地方长吏的根本不同在于,地方侠魁所依靠的是自己在本地的人脉和私人武力而非官方任命。他们出任地方武官的原因一是提高个人地位,二是利用官方的军队为私人武力赋予合法性。
总体而言,任侠与地方长吏地方实际支配权所进行的博弈本质上是已经逐渐衰弱的隋帝国公权和依靠实力建筑的地方私权间的对抗。
在隋帝国中央政府无力顾及地方情况下,公权力所代表的是帝国残存的公信力,而地方侠魁所面临的则是如何摆脱帝国的统治并把帝国公信力转化个人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