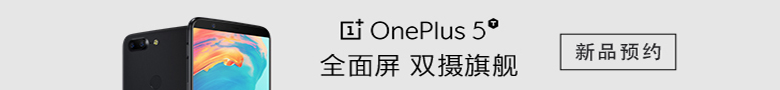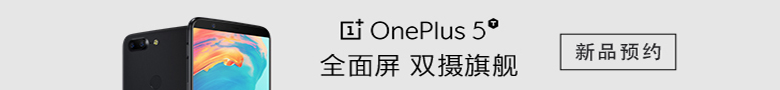纳粹德国的兴起,萨满巫师帮了很大的忙
纳粹德国的兴起,萨满巫师帮了很大的忙
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中,通过考古学和民俗学,以日耳曼人及其萨满传统作为德意志民族来历,着重日耳曼民族的独立发展,淡化甚至扼杀希腊、罗马影响的做法甚嚣尘上。能够说纳粹德国的兴起,日耳曼萨满是一个助力,希姆莱、戈林都是萨满爱好者。
请输入标题 bcdef
本文欢迎转载。
日耳曼史前史是纳粹政权活跃的时刻理论家们特别感兴趣的领域。
远古德意志帝国联盟是一个与罗森贝格办公室有密切联络的压力集团,它通过开发一种更具吸引力、信息量更大、更简单了解的展览形式,整合了前进日耳曼考古学知名度的种种尽力。
其意图是将日耳曼人千年间的日子演化描绘为既是一种能够抵挡外来影响的自我封闭和本土构成的现象,又是生动且挨近当代经历的事物。
纳粹独裁统治的前期见证了大学里的考古学和史前史学的迅速增长,在赫尔曼·戈林的公开支持下,这个学科在各个研讨组织和教育培训领域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戈林是一个萨满爱好者
考古和史前主题在教科书中非常杰出,并且在小说、电影和卡片的收会集引起了广泛重视,以致史前史能够被称为纳粹政权的宣扬“广告”。
并非政权中的每一个人都对日耳曼史前史抱有这样的热心。希特勒有时会对希姆莱对日耳曼考古学的热衷表明怀疑。
阿尔弗雷德·施佩尔回忆希特勒曾说过:
“当咱们的先人还住在泥屋里时,罗马人现已开端制作雄伟的修建,这现已够糟糕了;现在,希姆莱开端挖掘这些泥屋组成的村落,并对发现的每一块陶片和每一把石斧充满热心。”
希特勒本身对日耳曼民族连续性的认识在地理上不如希姆莱认识得具体。他的民族前史是一部千禧年叙事,其中第三帝国的成果必然会“再现”罗马帝国在权力巅峰时期的成果,这一观念反映在他对新古典主义办法的激烈偏好中,这种偏好从他为现在和未来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制作和规划的公共修建中体现出来。
希特勒是罗马次序爱好者
对萨满不伤风
但不阻碍他使用萨满
在这一点上,希特勒不同于那些热衷于德意志史前史的人(比方哈内),后者表扬北欧人和日耳曼人而反对罗马。
但无论选用哪一种变体,由此产生的时空图景的新颖性都是显而易见的:最近的魏玛政治史将变得极其悠远,而 新政权的千禧年溯源——或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或是日耳曼人在中欧和北欧久居的绵长而晦涩的前史,或是两者都有——看起来(或许应该看起来)非常近。
这个愿景在党卫队先人遗产研讨会的文明工作中被准则化了。但它也影响了许多地方行动者的议程。
在1937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吕内堡博物馆馆长格哈德·克尔纳声称,前一年公布的新种族法是最新的史前前史研讨的“界碑”,这门学科的主要方针有必要是“从头发现先人遗产”。
他接着说,研讨有必要习惯其时的需求,“这种习惯包括:用这种办法探究咱们先人的前史,以便从研讨中获得政治见地:使用文明遗产将研讨扩展到风俗和信仰,以探究咱们民族的共同之处和咱们民族的思想情感特质”。
在这种从头定位与将纳粹攫取政权的事件进行博物馆化展现的尽力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络,由于坐落哈雷的德国起义博物馆的馆长兼设计师哈内教授是新学科的重要倡导者,这门学科将史前日耳曼人移民研讨和人种学办法与民族的种族观念相结合,产生了一个关于日耳曼人在欧洲的起源和演化的超本质主义和生物学叙述。
关于这种研讨悠远过去的办法,哈内普及了“民族性研讨”这个概念。
1912年,他被任命为哈雷州立博物馆的馆长,这是一家建于1884年的尘封的组织,内有“图林根—萨克森前史与文物协会”的收藏品。在哈内的办理下,州立博物馆进行了改造:更名为民族性州立研讨所,新建了一座大型主楼,用于展现藏品和举行会议。
哈内率先开发了一种展览实践形式,能够对日耳曼民族的现在和史前前史之间的连续性进行可视化展现。地图、模型和图例被用来使零散的古代聚落变得生动。
哈内在1914年写道,他的意图是“揭示将咱们这些日子在当下的人与史前世界联络起来的头绪……,由于咱们今天的文明和咱们国家的史前文明首先是通过咱们与咱们先人的同一血统联络在一起的”。
除此之外,这也意味着与其时处于卓越位置的传统考古学存在敌对,反对将更先进的考古发现归因于罗马工艺或影响—— 哈内的许多早期著作重点驳斥了各种“罗马假说”,以保卫一种关于“独立存在的群体和文明圈”的、自主的“德意志考古学”,其共同性源自与特定自然环境建构起来的调和关系。
哈内对自己学科的了解一向是以民族为导向的,但直到一战结束后的几年,生物学和种族主义观念才开端主导他的思想。正是在这些年里,他成为“生物政治学”的拥护者,以为“民族科学是世界前史的基础和关键”。
哈内的前史观不是关于断裂、冲突和改变,而是关于以时节为标志的周期性存在的永久回归。 他被仍能在图林根的农村和小镇社区观察到的各种时节性典礼深深吸引。
例如奎斯腾节,一种听说起源于古日耳曼的公共典礼,与哈茨山脉的奎斯腾堡小镇有关:一个可能象征着太阳的花环被挂在一根10米高的杆子上,在每年五旬节当天的歌唱和庆祝活动中被焚烧和更换。
哈内和他的合作者成了风俗研讨的实践者,并记录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时节性典礼。哈内是如此喜爱这些典礼,以致创造了自己的“太阳节”和“年度表演”,他将《埃达》中的段落改编成剧本并交给当地的儿童乐团和青少年乐队表演。
古日耳曼人的如尼文
成了纳粹德国构建民族主义的魔法符文
哈内关于暗示了时刻深度和连续性的周期性时刻痕迹的深入了解,不仅仅是出于对知识的执着,这是一个摆脱前史窘境的避难所。
对哈内个人而言,这明显与一战的伤口有关,或许更精确地说,与战役在失败、经济骚动和政治骚动中惨白收场有关。
在1919年5月写给其母亲的一封信中,哈内表达了一种紊乱感:
“每一个清醒和沉睡的时刻,真的是每一个时刻,思想都处于一种混杂的、张狂的紊乱。如今,人们的‘思考’建立在情绪、身体状况和随机影响的基础之上,事实上直到得出结论也并没有通过任何真实的思想过程,由于到处都有‘假如’和‘但是’的带刺铁丝网。所以人们按部就班地做这一天、这一小时需求做的事情,什么都不去了解,在表面上抱有很多、很少或许不抱任何希望。”
在这封信里一段乖僻的文字中,哈内将他的痛苦与前史本身的观念交融在一起。
他写道,印刷机现已成了魔鬼的创作:“我再也不能爱谷登堡了,我简直想把他抹去——印刷机的创造真的是一种前进吗?对我来说,前进这个概念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愈加不可靠。”
伊利亚德所谓“前史的恐怖”也有相似的回响——一种极点异质性的状况,一种露出于随机性的骚动环境之下的焦虑状况,其结果是完全无法预见的。
前史学家罗特费尔斯以不同的办法提出了同样的观念,他观察到一战“对德国前史观念形成的冲击”促进前史学家开端寻求德国前史中的“范例”。
但对模范的推崇不可避免地按捺了偶然性,就像伊利亚德所说的“古风文明人”那样,“艰难地忍受‘前史’,并间歇性地试图废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