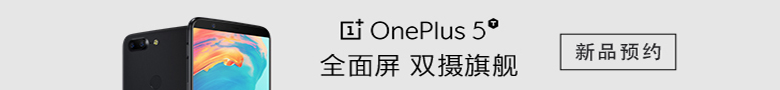罗家伦硬挖蒋廷黻,顾颉刚卖稿南下
罗家伦硬挖蒋廷黻,顾颉刚卖稿南下

高校如何“挖”教授
1929年夏天,时任职南开的何廉对于身边同事纷纷跳槽深感伤心,不禁惋惜道:“许多工作多年的关键的教师,包括萧遽、蒋廷黻、萧公权和李继侗一起离开南开去清华了,这对教学工作和学校的名声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高校间人才循环流动,学者们自谋发展天地,本是再自然不过之事。然虽皆是另攀新枝,每位教授之隐衷又各不相同,甚或尚有一把辛酸泪存其心中。故针对境遇迥异之教授,高校挖人手段可谓花样迭出。
不妨还是从何廉的二位同事蒋廷黻与萧公权讲起。蒋氏29岁赴南开任教,六年内发表的诸如《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统一方法的讨论》等论文,在学界反响颇大,实属冉冉升起之明星。当时罗家伦执掌清华,准备打造一支文科航母与北大相颉颃。所谓“航母”,无非广揽名角,形成规模优势,而带头人则显得愈发重要。放眼国内,罗氏认定年仅35岁的蒋廷黻独堪此任。于是其亲赴南开挖墙脚,来到蒋宅,劝其改投清华。蒋本来在南开干得好好的,不想离开天津。无奈罗施展软磨硬泡的功夫,“赖功”一流,坐着不走,整整熬了一夜。蒋廷黻终究拗不过罗家伦,答应赴清华任教。
后来,罗更是不惜开罪德高望重的中国史大家、章门高足、自己的恩师朱希祖,将系主任一职让与初来乍到的蒋廷黻。对于此事,罗后来回忆道:“纵然得罪了我的老师,但是我为了历史系的前途,也不能不为公义而牺牲私情了。”可见罗对蒋的期望之高。蒋亦不负罗之重托,在人才延揽方面费尽心思,罗织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学者,使清华历史系成为海内第一流的学系。据其同事陈之迈统计,当蒋于1935年离开清华时,历史系的阵容是:中国通史及古代史为雷海宗,隋唐史为陈寅恪,元史为姚从吾及邵循正,明史为吴晗,清史为萧一山,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为蒋廷黻,西洋史为刘寿民及张贵永,日本史为王信忠,俄国史为葛邦福(Michael Gapanovitch)。即使在今人眼中,此阵容也堪称梦幻级别了。
若蒋廷黻算被罗家伦“生拉硬拽”到清华的话,那么萧公权调任东北大学则属于“两厢情愿”型。初来南开,萧氏颇感惬意,享读书快乐之余,还深受友朋之乐。他与蒋廷黻、何廉、李继侗、姜立夫等同仁将学校百树村十号房改造成教员俱乐部。每到晚饭后,大家随意去那里喝咖啡,谈天,或作各种游艺,藉以稍纾一天工作的疲劳。娱乐一个小时左右,众人尽兴而返,“回家去继续作研究工作,或加紧预备教材”。
孰料佳期如梦,好景不长,不及三年,矛盾接踵而至。先是教学任务过大,“一位教授负责的教学包括四门、每周三个学时的不同课程,每周总共12节课。要胜任这么重的教学任务,备课工作是极其繁重的”。这势必分散学者的科研精力。接着学校在加薪事件上略有不公,令部分教授心寒,其中萧之堂兄萧叔玉负气北走清华,这让其也萌生退意。恰好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高惜冰受文法两院之托来天津延聘教授,萧就在挖人名单之列,且萧也有到关外走走之意,于是二者一拍即合。只是东北大学亦有其自身的问题,最严重的便是高校衙门化,官气甚浓。用萧的原话描述,“文学院和法学院两位院长的政治色彩似乎比较浓厚。整个大学好像都带有一点官府的气息。如果我们说南开办事的效率过高,我们只好说东北行政的效率太低”。一次,萧打算找院长商议公事,一名职员居然说:“拿名片来!”待萧将名片递给他,一看上面只印着姓名,并无显赫的头衔,这名职员便把名片往桌上一扔,口中甩出四个字:“院长不见!”普通职员对待堂堂大学教授竟毫无敬意,颐指气使。此情形,在当下的某些院校中是否亦似曾相识呢?萧氏自然受不了这股子官老爷做派,一年后便应燕京大学之邀,去北平发展。
萧氏在东北期间,曾遇到一段趣事。当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同在那里教书。东北大学的名誉校长乃少帅张学良。张见到林徽因这位女教授,顿时倾倒不已,嘱咐手下向她致意,并请其做家庭教师。二人本就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奉系“少帅”自然非民国“女神”的菜,林婉辞谢绝。等到学期结束,林立即同丈夫离开东北,被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挖走。这也算是“退避三舍”型了吧?
高校聘教授,自然是为了教书育人,繁荣学术。但高校亦是江湖,派系林立,纷争不已,故有时领导挖人又难免带有几分平衡校内势力的考虑。民国学人朱希祖身不由己的遭遇即是显例。
民初北大桐城派把持一时。为彻底打击此势力,北大校长何燏时从教育部将朱希祖挖来。其后朱利用同门情谊,陆续将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诸人聘至北大,章门弟子齐聚首,将桐城诸老之影响一扫而空。只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有风骚三五年,五四后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人渐成规模,至30年代已呈取章门而代之势头。此时朱希祖之处境便异常尴尬。1930年底,北大史学系学生出现要求朱辞职的风潮。迫于无奈,朱只得请辞。
落魄失意之际,朱曾经的学生、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负责人傅斯年伸出援手,力邀其加盟史语所担任专任研究员。不过傅尚有一条件,即朱必须完全与北大脱离关系,“院中规定专任研究员之待遇,一面固优为俸给,一面亦详为限定。盖专任者必不抱东牵西挂之意,然后可以济事,必以其自己之事业与研究所合为一体,然后可以成功。”然朱对北大仍有感情,于是保留一个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之虚衔。即使如此,傅却不依不饶,声称朱未践前诺,将其转为特约研究员。这相当于宣布朱希祖并非史语所正式人员。而此际,朱一没有在北大复职,二没有再去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兼职,三也未收到史语所正式聘书,真真正正在北平下岗了。其实傅将朱挖过来之本意,在于彻底肃清太炎弟子在北大文科之势力。又怎能容忍朱同北大还留有一丝联系?
据朱希祖儿子回忆,“老人家因和北方的学阀们相处得不大好,新近受了傅斯年一批学棍的排挤,把他调离了北京大学,这学年甚至没有能够开课,所以心境十分不佳。”直到1932年10月,朱不得不接受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聘请,南下广州任教授。至此,朱方走出学术低谷。
其实,对于高校而言,人才流动实属平常,但落到个人身上,却往往不平常,其间的缘由并非皆足与人道。是故,每个曾经被挖或出走的教授,都是有故事的人呐!

高校如何“挖”教授
后来,罗更是不惜开罪德高望重的中国史大家、章门高足、自己的恩师朱希祖,将系主任一职让与初来乍到的蒋廷黻。对于此事,罗后来回忆道:“纵然得罪了我的老师,但是我为了历史系的前途,也不能不为公义而牺牲私情了。”可见罗对蒋的期望之高。蒋亦不负罗之重托,在人才延揽方面费尽心思,罗织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学者,使清华历史系成为海内第一流的学系。据其同事陈之迈统计,当蒋于1935年离开清华时,历史系的阵容是:中国通史及古代史为雷海宗,隋唐史为陈寅恪,元史为姚从吾及邵循正,明史为吴晗,清史为萧一山,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为蒋廷黻,西洋史为刘寿民及张贵永,日本史为王信忠,俄国史为葛邦福(Michael Gapanovitch)。即使在今人眼中,此阵容也堪称梦幻级别了。
孰料佳期如梦,好景不长,不及三年,矛盾接踵而至。先是教学任务过大,“一位教授负责的教学包括四门、每周三个学时的不同课程,每周总共12节课。要胜任这么重的教学任务,备课工作是极其繁重的”。这势必分散学者的科研精力。接着学校在加薪事件上略有不公,令部分教授心寒,其中萧之堂兄萧叔玉负气北走清华,这让其也萌生退意。恰好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高惜冰受文法两院之托来天津延聘教授,萧就在挖人名单之列,且萧也有到关外走走之意,于是二者一拍即合。只是东北大学亦有其自身的问题,最严重的便是高校衙门化,官气甚浓。用萧的原话描述,“文学院和法学院两位院长的政治色彩似乎比较浓厚。整个大学好像都带有一点官府的气息。如果我们说南开办事的效率过高,我们只好说东北行政的效率太低”。一次,萧打算找院长商议公事,一名职员居然说:“拿名片来!”待萧将名片递给他,一看上面只印着姓名,并无显赫的头衔,这名职员便把名片往桌上一扔,口中甩出四个字:“院长不见!”普通职员对待堂堂大学教授竟毫无敬意,颐指气使。此情形,在当下的某些院校中是否亦似曾相识呢?萧氏自然受不了这股子官老爷做派,一年后便应燕京大学之邀,去北平发展。
落魄失意之际,朱曾经的学生、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负责人傅斯年伸出援手,力邀其加盟史语所担任专任研究员。不过傅尚有一条件,即朱必须完全与北大脱离关系,“院中规定专任研究员之待遇,一面固优为俸给,一面亦详为限定。盖专任者必不抱东牵西挂之意,然后可以济事,必以其自己之事业与研究所合为一体,然后可以成功。”然朱对北大仍有感情,于是保留一个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之虚衔。即使如此,傅却不依不饶,声称朱未践前诺,将其转为特约研究员。这相当于宣布朱希祖并非史语所正式人员。而此际,朱一没有在北大复职,二没有再去清华大学、辅仁大学兼职,三也未收到史语所正式聘书,真真正正在北平下岗了。其实傅将朱挖过来之本意,在于彻底肃清太炎弟子在北大文科之势力。又怎能容忍朱同北大还留有一丝联系?
标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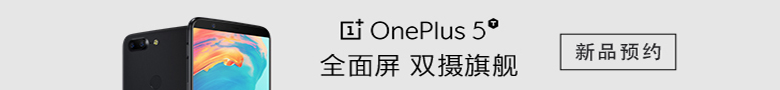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