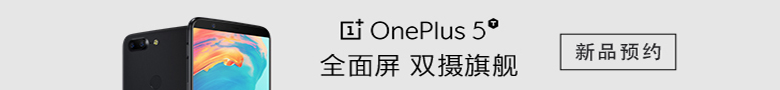论天台山佛教圣地化的初期历史
论天台山佛教圣地化的初期历史
摘 要:东晋南北朝时期天台山作为五百罗汉圣地的塑造,远早于中土山岳菩萨道场的构建。在中国传统东西神圣空间的对称格局下,借助道教“洞天福地—神仙治所”的理论,佛教中的阿耨达池五百罗汉实现了“东迁”与“南渡”,最终变成天台山五百罗汉。北齐《赵郡王高叡修寺碑》中“远住东海”的“金台罗汉”就是天台山五百罗汉,他们也是《首罗比丘经》中得见月光童子出世的五百仙人。
关键词:五百罗汉;天台山;月光童子;五百仙人;弥勒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汉唐时期中国罗汉信仰研究”(18YJC730005)阶段性成果。
东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宗教史上第一个关键期,佛教由域外输入、传播,道教在本土产生、发展,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民族融合的时代背景,造就了这一时期异常复杂的文化面貌。罗汉信仰在唐以前的流传情况,因为留下的资料十分零散、稀少,一直未能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以北齐《赵郡王高叡修寺碑》中涉及罗汉的内容为切入点,就天台山作为五百罗汉道场被塑造和接受的初期历史予以阐明,以期对中国佛教圣地的构建策略与过程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
一、《赵郡王高叡修寺碑》碑名考订
河北灵寿县幽居寺遗址保留古碑四通(北齐碑二、元碑二),分别是《大齐赵郡王□□□之碑》、《赵郡王高叡修寺颂记》,及《大元历代圣主恩慧抚护之碑》(祁林院圣旨碑)和《大元国皇太后懿旨》。据两通元碑,元代时此寺已称“祇(祁)林院”或“幽居寺”,这一称呼沿袭至今。《大齐赵郡王□□□之碑》因碑额脱落三字,自清代道光年间出土后,一直没有统一的命名,且一度“以讹传讹”。在进入本文主题之前,实在有必要先考订碑名,纠正其中的谬误。
翁方纲(1733-1818)《跋北齐祁林山寺碑》是目前所见记录该碑最早的文献,翁氏言“北齐祁林山寺碑”是从该碑当时所处地名的角度对它的直接称呼,并非对其正式命名。细观跋文,“北齐赵郡王高叡建寺之碑”是他对该碑的真正认知。当然,此寺并非高叡始建,所以翁氏“高叡建寺之碑”的称呼并不妥。翁氏所见碑本乃黄易(1744-1802)相赠,跋文多言黄易拓碑之艰,“以地僻多虎,不可再拓”1。
等到沈涛(约1792-1855)撰写《常山贞石志》时,已将该碑命名为《赵郡王高叡修寺碑》。2在不能确知此碑准确名称之前,可以说沈涛的这一命名最为妥当。然不知何时始,清代文坛却流行起“定国寺碑”的讹称。
陆增祥(1816-1882)《八琼室金石补正》将此碑定名为《高叡定国寺塔铭碑》,云:
今碑在祁林山祁林院,院一名幽居寺,盖灵寿古刹也。《灵寿县志》云:祁林山在县西北一百十一里,北齐赵郡王高叡,历选太行胜概,得朱山之阳,建祁林寺,置僧舍二百余间,择行僧二千余众居之。齐亡寺亦荒废,继盛于元大德间。碑云定州定国寺禅师僧标以其山处闲虚,林幽爽旷,乃施净财,云为禅室,于兹廿有余年。据此则此寺实创于东魏天平初,及赵郡王刺定州时拓而新之,更建灵塔。县志误以寺为叡所创造,特未见此碑故耳。3
陆氏对《灵寿县志》的纠正无疑是对的,然而他在对《常山贞石志》补缺正讹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沈涛对碑名的谨慎态度。因该寺始建于定国寺僧人僧标,所以误将此寺认为定国寺。定国寺为北齐著名官寺,东魏武定年间由高欢(496-547)主持修建,与该寺绝非一处。这点李慈铭(1830-1894)在《北齐定国寺碑铭跋》中就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僧标本为定州定国寺僧,爱北山闲旷,因结禅室,叡始为之置田立寺名,其字虽不可辨,决非定国二字。且以宣尼四语文意推之,亦非定国之义。故荷屋题为高叡修佛寺碑,不云定国寺碑也。”4李氏注意到碑文“因以其寺,名粤(曰)□□。宣尼论至道之时,乃有斯称。轩辕念天师之教,且苻(符)今旨。”5名粤(曰)之后脱落两字即原本寺名,根据宣尼、轩辕两句文意看,绝非定国。李氏特别提到吴荣光(1773-1843,号荷屋)将该碑题为“高叡修佛寺碑”而“不云定国寺碑”。吴荣光活动时间略早于沈涛,沈涛对该碑的命名是否受他影响尚不得而知。
即便有李慈铭对碑名误定的警醒与阐发,然而从他所跋为“北齐定国寺碑铭”来看,19世纪下半叶这一讹称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了。随着后来《八琼室金石补正》的刊刻流传,这一讹称可以说几成定势,为当今关注此碑的学者所沿用。孙贯文遗作《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就将此碑称为“赵郡王修定国寺塔碑”6,颜娟英在其主编《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中也称该碑为“赵郡王高叡定国寺碑”7。刘建华虽将此碑称为“赵郡王高睿修寺之碑”,却又受《八琼室金石补正》误导,认为此寺即定州定国寺,元代改称祁林院或幽居寺。8魏斌亦沿用《八琼室金石补正》,称该碑为“赵郡王高叡定国寺塔铭碑”。9而丁明夷在其所著《佛教新出碑志集萃》中沿袭《常山贞石志》,称该碑为“赵郡王高叡修寺碑”,不言定国寺,殊为可贵。不过他又在注释中说:“该碑额题作《大齐赵郡王□□□之碑》,其中脱落三字,疑为‘幽居寺’。”10倘若我们以李慈铭提示“以宣尼四语文意推之”那原本寺名也绝非“幽居”二字,祁林院和幽居寺之称当为晚出。
综上,在没有新资料出现之前,沿用《常山贞石志》中“赵郡王高叡修寺碑”这一碑名最为合适,定国寺碑名虽然流传广、沿袭多,但因确实有误,不宜从之。
高叡为北齐高祖、神武帝高欢弟赵郡王高琛之子,《北齐书》及《北史》皆有传。高叡崇佛,天保七年(556)高叡以“使持节、都督定瀛幽沧安平东燕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赵郡王”的身份修寺,并于寺内为其亡伯献武皇帝高欢、亡兄文襄皇帝高澄造释迦像一躯,为其亡父高琛、亡母华阳郡长公主元氏造无量寿佛像一躯,为己身及妃郑氏造阿閦佛像一躯。天保八年(557)所立《赵郡王高叡修寺碑》和《赵郡王高叡修寺颂记》即缘于斯事。本文无意对《赵郡王高叡修寺碑》作整体解读,而仅就其中涉及罗汉以及与罗汉相关的月光童子部分展开专题探讨。这方面碑文内容虽然极少,然而信息量大,意涵丰富,反映出6世纪中土信仰世界的方位变迁以及月光童子与弥勒信仰、罗汉信仰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十分重要。
二、西域五百罗汉的东迁与南渡
《赵郡王高睿修寺碑》云:“金台罗汉,远住东海;琼树声闻,遥家西域。”11本文认为,这里“远住东海”的“金台罗汉”当为天台山五百罗汉,而“遥家西域”的“琼树声闻”则指昆仑山阿耨达池五百罗汉或罽宾国五百罗汉。后一组罗汉于释典有征,而前一组则是随着中国东西方位神话变迁而产生的“神仙侨民”12,简言之是后一组的东迁与南渡。
中土对西域五百罗汉的认识较早。东汉康孟祥译《佛说兴起行经》序中说,昆仑山周匝有五百黄金窟,五百罗汉常居之,在昆仑山上的阿耨达池(又称阿耨大泉)中有金台,台上有金莲花,如来带领五百罗汉,常以每月十五日于中说戒,舍利弗于此问佛十事宿缘,“又阿耨泉中非有漏、碍形所可周旋,唯有阿难为如来所接也”。13西晋竺法护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载,阿耨达池龙王常请佛及五百上首弟子于阿耨达池用膳、讲法。14可见,这里的阿耨达池五百罗汉为佛陀在世时的五百上首弟子,包括舍利弗、阿难等。
到5世纪初,中土僧人又了解到罽宾国五百罗汉。西行求法的智猛,在其记述游历事迹的《外国传》中提到罽宾国有五百罗汉“常往返阿耨达池”15,据智猛所述,则罽宾国五百罗汉与阿耨达池五百罗汉似为同一组。梁代宝唱所撰《名僧传》记载了凉州人僧表因听闻罽宾恒有五百罗汉供养佛钵,“乃西逾葱岭,欲致诚礼”16。而通过宝唱的另一部僧人传记我们知道,南朝比丘尼净秀曾供请阿耨达池五百罗汉和罽宾国五百罗汉。17此事亦见于沈约(441-513)为净秀所作行状:
此后又请阿耨达池五百罗汉,日日凡圣无遮大会,已近二旬,供设既丰。复更请罽宾国五百罗汉,足上为千,及请凡僧还如前法,始过一日,见有一外国道人,众僧悉皆不识,于是试相借问,自云:“从罽宾国来。”又问:“来此几时?”答云:“来始一年也。”众僧觉异,令人守门观其动静,而食毕乃于宋林门出,使人逐视,见从宋林门去,行十余步,奄便失之。18
净秀分别请阿耨达池五百罗汉和罽宾国五百罗汉,则他们应是不同的两组罗汉。而在请罽宾国五百罗汉的这场法会上,有位自称来自罽宾的外国道人,从其神异表现来看,当为前来应供的罗汉。可见,当时的中土信众相信,通过特定的仪式可以感召西域五百罗汉(可能是其中的一位)前来应供。他们以胡僧的形貌悄悄出现在法会中,一旦被认出便消失不见。宝唱曾撰《饭圣僧法》五卷19,已佚,就此推测,很可能就是供请阿耨达池五百罗汉和罽宾国五百罗汉的仪式文本。
另外,6世纪初中土求法僧在乌场国(印度北部边境山国乌仗那国)也见到了五百罗汉的遗迹。北魏神龟二年(519),西行取经的僧人惠生和宋云到了乌场国,在王城西南五百里的善持山中见到“有昔五百罗汉床,南北两行,相向坐处,其次第相对”20。
通过对6世纪以前中土译经及撰述中有关西域五百罗汉记载的考察和梳理,可以发现:第一,中土有对西域五百罗汉(阿耨达池五百罗汉和罽宾国五百罗汉)的供养法会和仪式文本;第二,信徒可以感遇或者得见罗汉,他们往往化作凡僧与信众打交道(赴斋);第三,此时出现的五百罗汉皆为外国人的身份,并居住在西域。无论是五百罗汉的外国人身份,还是他们远在千万里之外的居所,都不能充分满足中土信众的信仰心理和宗教情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本土化的五百罗汉信仰很快便开始出现,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为这外来的五百罗汉在中土“安家”。
五百罗汉在中土的居所,最著名者乃天台山。学者多认为天台山作为五百罗汉居所的确立是五代以后的事,但是我们以为,这个时间很可能要提前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天台山为圣人居所之说早已有之,东晋孙绰(314-371)《游天台山赋》将天台山与蓬莱相比:“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21李丰楙认为,西方系的昆仑山神话与东方系的蓬莱山神话开始只是各自独立发展,后来依据东西方位的对称逐渐构成神话舆图上神圣空间的对称,由于东方系的蓬瀛在影响上相对弱势,加之东晋政权南移,“滨海地域”的东方圣山出现多位且“一时之间显得游移不定”22,这正是江南地区天台山兴起的背景以及常与蓬莱山相提并论的深层原因。《赵郡王高睿修寺碑》首句即言:“珠林璇室,现昆仑之中;银阙金宫,跱蓬莱之上。”可见李氏所言甚是,这种东西对称的神圣空间格局已成为中土信仰世界的共识。
孙绰文中还说天台山同时为佛道圣者所居:“王乔控鹤以冲天,应真飞锡以蹑虚。”23王乔,即王子乔,为道教中的仙人,《后汉书》卷二十八下《冯衍传》“庶几乎松乔之福”条注引《列仙传》:“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之间,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遂仙去也。”24关于王子乔的信仰地理为何从洛阳附近迁移到了会稽的天台山,魏斌称其为“神仙侨民”的南渡叙事,可能主要是在永嘉乱后流民南迁的背景下出现的。25应真,即罗汉的另一种译名。罗汉这一概念最早输入中国时就被理解为能够飞升幻化的神仙,东汉时出现的《四十二章经》对罗汉的解释就是“能飞行变化,住寿命,动天地”26。伴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出现了一类受佛嘱咐、不入涅槃的住世(寿)罗汉,这种主张很快与中国传统的神仙信仰相结合,为向来喜欢追求长生不死的中国人所接受。“东晋南朝时期天台山神仙洞府想象的核心,是桐柏真人王子乔的金庭馆和金庭洞宫。”27本文认为,《赵郡王高睿修寺碑》中的“金台”即源于这里的“金庭”,而佛教徒将神仙洞府的主人由神仙真人替换为罗汉声闻,采取的策略正是在东西对称的信仰传统下将昆仑山阿耨达池上金台中的五百罗汉搬迁于此。
天台山为罗汉圣地之说虽早已流行,但五百之数究竟有何凭证?梁代慧皎所撰《高僧传》中记载了东晋太元年间(376-396)僧人竺昙猷度过天台石桥、得遇圣寺神僧的故事,未言圣僧数目。同书还记有竺道潜(286-374)的弟子竺法友,“尝从深受阿毘昙,一宿便诵。深曰:‘经目则讽,见称昔人;若能仁更兴大晋者,必取汝为五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讲说。后立剡县城南台寺焉”。28道潜说法友为五百罗汉之一,考虑到他们活动在天台山附近,而道潜僧团与孙绰也有来往,道潜所说“五百”很可能就是天台山五百罗汉,当时浙东文化圈对于天台山五百罗汉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此外,对月光童子信仰的考察也可以为我们理解东晋南北朝时期天台山作为五百罗汉道场的地位提供新的线索和思路。《赵郡王高叡修佛寺碑》中云:“月光童子戏天台之傍,仁祠浮图绕嵩高之侧。”29魏斌已经注意到月光童子与天台山的关系,但他并未就这一关系对天台山作为五百罗汉圣地的意义进行引申。下面,我们将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论述。
三、月光童子信仰与天台山的圣地化
除了《赵郡王高叡修寺碑》外,至迟6世纪初已出现的伪经《首罗比丘见五百仙人并见月光童子经》中已有月光童子活动于天台山的记载:“首罗问大仙曰:‘月光出世当用何时?’‘古月末后,时出境阳,普告诸贤者:天台山引路游观,至介斧山,又到闵子窟列鲁簿:一号太山,二号真君,三号缕练郡圣。’”30将这段经文与疑为寇谦之(365-448)所撰《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相比较:
天尊言:我在宫中观万民,作善者少,兴恶者多。大劫欲末,天尊遣八部监察,以甲申年正月十五日诣太山主簿,共算世间名籍。有修福建斋者,三阳地男女八百人得道,北方魏都地千三百人得道,秦川汉地三百五十人得道,长安晋地男女二百八十七人得道。31
明显可见《首罗比丘经》受到道教“定录成仙”思想的影响。《初学记》卷五《地部上·嵩高山》引卢元明《嵩山记》:“月光童子常在天台,亦来于此。”32前述道教真人王子乔的信仰地理由嵩山移到天台山,而这里月光童子的活动空间也常在两地往来,月光童子的这一特征或许受到了王子乔故事的启发和影响。姜望来指出,东西政权对峙格局形成后,高氏与宇文氏分别采取重佛和重道的宗教政策,北朝道教发展重心由东而西,华岳取代嵩岳成为北朝后期北方道教中心,卢元明(大致活动于北魏末东魏初)撰写《嵩山记》正值道教在佛教进攻下退出嵩岳之时,月光童子由天台山往来于嵩山正是佛教占领嵩岳的写照。33罗汉居所的东迁与道教重心的西移,月光童子的北上与道教神仙的南下,这种相悖与冲突想来绝非偶然,正是两教在传播过程中争夺地域与信众的反映,而分裂变化的政治背景和人口流动的社会环境又在其中起到了牵引推动的作用。
再回到《首罗比丘经》,首罗说五百仙人“烦恼永尽”,且君子国王及大臣“倾心西望而不可止:‘西国真人修何功德,得值入善?作何善业,得见月光出世?而我国人远而不见?’”34五百仙人为“烦恼永尽”的“真人”,足见他们即五百罗汉,而“西望”“西国”又说明他们是西来者,即西域五百罗汉。南岳大师慧思(515-577)立誓愿文中有“自非神仙,不得久住”“为护法故求长命”“作长寿仙见弥勒”35,可见他认为那些住世(寿)护法以待弥勒出世的罗汉即神仙、长寿仙。将长寿神仙与住世罗汉相提并论、等而视之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普遍认识,因此这一时期中土造作的《首罗比丘经》将五百罗汉称为五百仙人也就不足为奇,何况该经本就受到道教成仙思想的影响。《首罗比丘经》说西国五百仙人(即西域五百罗汉)得见月光童子出世,而月光童子与五百罗汉的关系则源于月光童子与弥勒在神格上的同质性。杨惠南就曾指出,月光童子与弥勒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二者在中国政治史上几乎合二为一。36
弥勒信仰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极为兴盛,且有两点鲜明特征;一是弥勒信仰与住世罗汉紧密相关,住世罗汉往往扮演弥勒使者的角色;二是关于弥勒净土的方位多认为在西北高空,这又与前述中土信仰舆图中的昆仑山以及五百罗汉的“老家”一致。东晋名僧道安为弥勒信仰者,他曾于弥勒像前立誓,愿生兜率,后遇异僧,道安问其“来生所往处”,异僧“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报”,该异僧正是“不得入涅槃,住在西域”的“胡道人”宾头卢。37据北凉道泰所译《入大乘论》,“尊者宾头卢、尊者罗睺罗,如是等十六人诸大声闻散在诸渚,于余经中亦说有九十九亿大阿罗汉,皆于佛前取筹护法,住寿于世界”38。曾获赵郡王高叡等北齐懿戚重臣敬奉的僧人昙衍,临终时“诵念弥勒佛声气俱尽”,而其“未终之前,有梦见衍朱衣螺发颁垂于背,二童侍之升空而西北高逝。寻而便终,时共以为天道者矣。”39分享了弥勒神格特质的月光童子带领五百仙人活动在天台山,这一信仰的诞生是整合了当时已有信仰资源发展出来的。在中国传统东西神圣空间对称、联动的背景下,天台山作为滨海地域的东方系其地位日益重要,成为佛道两教的共同圣地。因为罗汉与神仙在长寿、住世等方面的相类,佛教在道教神仙洞府叙事之外开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圣寺神僧主题。
四、结论
魏斌指出,道教领域内积累发展的山岳认识和神仙洞府想象,在佛教领域内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为此,“洞天福地—神仙治所”构想是否影响到后来山岳菩萨道场的形成,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40其实,早在山岳菩萨道场形成之前,佛教率先把罗汉的住处从“远方夷狄之洞”41搬迁到中土“圣果福地”42。在中国佛教圣地的构建史上,罗汉道场的确立,其时间要远远早于菩萨道场。虽然唐代五台山和峨眉山作为两大佛教名山已被并称43,可是它们文殊和普贤道场的身份尚未被普遍接受。这在道士徐灵府的《天台山记》中有所体现:“今游人所见者正是北桥也,是罗汉所居之所也,意为即小者,则不知大者复在何处,盖神仙冥隐,非常人所睹。”44罗汉是“小者”,菩萨是“大者”,徐灵府很明确天台山作为罗汉居所的地位,却不知晓菩萨住在何处。一方面,这确实与徐灵府常年活动在天台山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天台山作为罗汉道场之说起源早,流传广,唐代时已经累积成一种社会共识,而文殊菩萨领一万菩萨居住在五台山的观念则刚确立不久,仍需时间积淀与传播。因此,有学者认为“天台山被形塑成五百罗汉居住之地,可能也有和五台山相抗衡的意味”45,这种观点恐怕不能成立。
东晋南北朝时期开创于天台山的中土罗汉山岳道场思想,一直流行于隋唐两宋,且在天台山之外,还有罗汉居于其他名山的传闻。据宋崇宁元年(1102)释有挺撰《五百大阿罗汉洞记》(又名《修圣竹林寺碑》),唐初蜀僧法藏感得灵异,获知嵩山竹林寺是罗汉所居的圣寺。46以竹林命名罗汉圣寺早在唐代道宣笔下就有,《律相感通传》中鼓山竹林寺即是由山神从佛请五百罗汉所住。“竹林”成为与“龙池”(即阿耨达池)相类的一种灵境。47除了竹林寺外,山岳中的罗汉道场还有方广寺之名。宋代道士陈田夫所撰《南岳总胜集》记有梁代僧人希遁在天台山遇到五百罗汉之一的慧海尊者,并在他的指引下得入五百罗汉道场——南岳方广寺的故事48。该书还称,在莲花峰北灵辙源有鬼神为罗汉运粮留下来的车辙道。49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天台山的五百罗汉道场也开始有了方广寺的名字。刘淑芬认为,“天台山方广寺之称可能源自南岳衡山”45。宋元符元年(1098)五百罗汉圣号碑言“天台山南岳车辙灵须方广寺内五百大阿罗汉”50,可见二者确实有关。南岳慧海尊者作为五百罗汉的代表,其名号赫然列在明代僧人紫柏(1543-1603)所撰《礼佛仪式》中51,这又是罗汉信仰在中国化过程中另一个层面的表现了。
除了嵩山、衡山外,峨眉、五台、庐山52以及罗浮山、茅山53等皆有罗汉居住的传闻。当然,这些都没有影响到天台山的地位。宋代之后天台山方广寺成为五百罗汉最著名的道场,与五台山相提并论,影响远播海外,这在日僧成寻的求法日记中可见一斑。54天台山这一在东晋南北朝即作为罗汉道场的佛教圣地终于成为东亚佛教文化圈中的重要地理坐标,只是在东西神圣空间的对称格局之下罗汉们如何借助道教神仙思想而从西域迁来的过程已经淹没无闻,幸得《赵郡王高叡修寺碑》等文献中保留的只言片语,为我们更多地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摘 要:东晋南北朝时期天台山作为五百罗汉圣地的塑造,远早于中土山岳菩萨道场的构建。在中国传统东西神圣空间的对称格局下,借助道教“洞天福地—神仙治所”的理论,佛教中的阿耨达池五百罗汉实现了“东迁”与“南渡”,最终变成天台山五百罗汉。北齐《赵郡王高叡修寺碑》中“远住东海”的“金台罗汉”就是天台山五百罗汉,他们也是《首罗比丘经》中得见月光童子出世的五百仙人。
关键词:五百罗汉;天台山;月光童子;五百仙人;弥勒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汉唐时期中国罗汉信仰研究”(18YJC730005)阶段性成果。
东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宗教史上第一个关键期,佛教由域外输入、传播,道教在本土产生、发展,南北分裂的政治格局,民族融合的时代背景,造就了这一时期异常复杂的文化面貌。罗汉信仰在唐以前的流传情况,因为留下的资料十分零散、稀少,一直未能引起学界的关注。本文以北齐《赵郡王高叡修寺碑》中涉及罗汉的内容为切入点,就天台山作为五百罗汉道场被塑造和接受的初期历史予以阐明,以期对中国佛教圣地的构建策略与过程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
一、《赵郡王高叡修寺碑》碑名考订
河北灵寿县幽居寺遗址保留古碑四通(北齐碑二、元碑二),分别是《大齐赵郡王□□□之碑》、《赵郡王高叡修寺颂记》,及《大元历代圣主恩慧抚护之碑》(祁林院圣旨碑)和《大元国皇太后懿旨》。据两通元碑,元代时此寺已称“祇(祁)林院”或“幽居寺”,这一称呼沿袭至今。《大齐赵郡王□□□之碑》因碑额脱落三字,自清代道光年间出土后,一直没有统一的命名,且一度“以讹传讹”。在进入本文主题之前,实在有必要先考订碑名,纠正其中的谬误。
翁方纲(1733-1818)《跋北齐祁林山寺碑》是目前所见记录该碑最早的文献,翁氏言“北齐祁林山寺碑”是从该碑当时所处地名的角度对它的直接称呼,并非对其正式命名。细观跋文,“北齐赵郡王高叡建寺之碑”是他对该碑的真正认知。当然,此寺并非高叡始建,所以翁氏“高叡建寺之碑”的称呼并不妥。翁氏所见碑本乃黄易(1744-1802)相赠,跋文多言黄易拓碑之艰,“以地僻多虎,不可再拓”1。
等到沈涛(约1792-1855)撰写《常山贞石志》时,已将该碑命名为《赵郡王高叡修寺碑》。2在不能确知此碑准确名称之前,可以说沈涛的这一命名最为妥当。然不知何时始,清代文坛却流行起“定国寺碑”的讹称。
陆增祥(1816-1882)《八琼室金石补正》将此碑定名为《高叡定国寺塔铭碑》,云:
今碑在祁林山祁林院,院一名幽居寺,盖灵寿古刹也。《灵寿县志》云:祁林山在县西北一百十一里,北齐赵郡王高叡,历选太行胜概,得朱山之阳,建祁林寺,置僧舍二百余间,择行僧二千余众居之。齐亡寺亦荒废,继盛于元大德间。碑云定州定国寺禅师僧标以其山处闲虚,林幽爽旷,乃施净财,云为禅室,于兹廿有余年。据此则此寺实创于东魏天平初,及赵郡王刺定州时拓而新之,更建灵塔。县志误以寺为叡所创造,特未见此碑故耳。3
陆氏对《灵寿县志》的纠正无疑是对的,然而他在对《常山贞石志》补缺正讹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沈涛对碑名的谨慎态度。因该寺始建于定国寺僧人僧标,所以误将此寺认为定国寺。定国寺为北齐著名官寺,东魏武定年间由高欢(496-547)主持修建,与该寺绝非一处。这点李慈铭(1830-1894)在《北齐定国寺碑铭跋》中就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僧标本为定州定国寺僧,爱北山闲旷,因结禅室,叡始为之置田立寺名,其字虽不可辨,决非定国二字。且以宣尼四语文意推之,亦非定国之义。故荷屋题为高叡修佛寺碑,不云定国寺碑也。”4李氏注意到碑文“因以其寺,名粤(曰)□□。宣尼论至道之时,乃有斯称。轩辕念天师之教,且苻(符)今旨。”5名粤(曰)之后脱落两字即原本寺名,根据宣尼、轩辕两句文意看,绝非定国。李氏特别提到吴荣光(1773-1843,号荷屋)将该碑题为“高叡修佛寺碑”而“不云定国寺碑”。吴荣光活动时间略早于沈涛,沈涛对该碑的命名是否受他影响尚不得而知。
即便有李慈铭对碑名误定的警醒与阐发,然而从他所跋为“北齐定国寺碑铭”来看,19世纪下半叶这一讹称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了。随着后来《八琼室金石补正》的刊刻流传,这一讹称可以说几成定势,为当今关注此碑的学者所沿用。孙贯文遗作《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就将此碑称为“赵郡王修定国寺塔碑”6,颜娟英在其主编《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中也称该碑为“赵郡王高叡定国寺碑”7。刘建华虽将此碑称为“赵郡王高睿修寺之碑”,却又受《八琼室金石补正》误导,认为此寺即定州定国寺,元代改称祁林院或幽居寺。8魏斌亦沿用《八琼室金石补正》,称该碑为“赵郡王高叡定国寺塔铭碑”。9而丁明夷在其所著《佛教新出碑志集萃》中沿袭《常山贞石志》,称该碑为“赵郡王高叡修寺碑”,不言定国寺,殊为可贵。不过他又在注释中说:“该碑额题作《大齐赵郡王□□□之碑》,其中脱落三字,疑为‘幽居寺’。”10倘若我们以李慈铭提示“以宣尼四语文意推之”那原本寺名也绝非“幽居”二字,祁林院和幽居寺之称当为晚出。
综上,在没有新资料出现之前,沿用《常山贞石志》中“赵郡王高叡修寺碑”这一碑名最为合适,定国寺碑名虽然流传广、沿袭多,但因确实有误,不宜从之。
高叡为北齐高祖、神武帝高欢弟赵郡王高琛之子,《北齐书》及《北史》皆有传。高叡崇佛,天保七年(556)高叡以“使持节、都督定瀛幽沧安平东燕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赵郡王”的身份修寺,并于寺内为其亡伯献武皇帝高欢、亡兄文襄皇帝高澄造释迦像一躯,为其亡父高琛、亡母华阳郡长公主元氏造无量寿佛像一躯,为己身及妃郑氏造阿閦佛像一躯。天保八年(557)所立《赵郡王高叡修寺碑》和《赵郡王高叡修寺颂记》即缘于斯事。本文无意对《赵郡王高叡修寺碑》作整体解读,而仅就其中涉及罗汉以及与罗汉相关的月光童子部分展开专题探讨。这方面碑文内容虽然极少,然而信息量大,意涵丰富,反映出6世纪中土信仰世界的方位变迁以及月光童子与弥勒信仰、罗汉信仰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十分重要。
二、西域五百罗汉的东迁与南渡
《赵郡王高睿修寺碑》云:“金台罗汉,远住东海;琼树声闻,遥家西域。”11本文认为,这里“远住东海”的“金台罗汉”当为天台山五百罗汉,而“遥家西域”的“琼树声闻”则指昆仑山阿耨达池五百罗汉或罽宾国五百罗汉。后一组罗汉于释典有征,而前一组则是随着中国东西方位神话变迁而产生的“神仙侨民”12,简言之是后一组的东迁与南渡。
中土对西域五百罗汉的认识较早。东汉康孟祥译《佛说兴起行经》序中说,昆仑山周匝有五百黄金窟,五百罗汉常居之,在昆仑山上的阿耨达池(又称阿耨大泉)中有金台,台上有金莲花,如来带领五百罗汉,常以每月十五日于中说戒,舍利弗于此问佛十事宿缘,“又阿耨泉中非有漏、碍形所可周旋,唯有阿难为如来所接也”。13西晋竺法护译《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载,阿耨达池龙王常请佛及五百上首弟子于阿耨达池用膳、讲法。14可见,这里的阿耨达池五百罗汉为佛陀在世时的五百上首弟子,包括舍利弗、阿难等。
到5世纪初,中土僧人又了解到罽宾国五百罗汉。西行求法的智猛,在其记述游历事迹的《外国传》中提到罽宾国有五百罗汉“常往返阿耨达池”15,据智猛所述,则罽宾国五百罗汉与阿耨达池五百罗汉似为同一组。梁代宝唱所撰《名僧传》记载了凉州人僧表因听闻罽宾恒有五百罗汉供养佛钵,“乃西逾葱岭,欲致诚礼”16。而通过宝唱的另一部僧人传记我们知道,南朝比丘尼净秀曾供请阿耨达池五百罗汉和罽宾国五百罗汉。17此事亦见于沈约(441-513)为净秀所作行状:
此后又请阿耨达池五百罗汉,日日凡圣无遮大会,已近二旬,供设既丰。复更请罽宾国五百罗汉,足上为千,及请凡僧还如前法,始过一日,见有一外国道人,众僧悉皆不识,于是试相借问,自云:“从罽宾国来。”又问:“来此几时?”答云:“来始一年也。”众僧觉异,令人守门观其动静,而食毕乃于宋林门出,使人逐视,见从宋林门去,行十余步,奄便失之。18
净秀分别请阿耨达池五百罗汉和罽宾国五百罗汉,则他们应是不同的两组罗汉。而在请罽宾国五百罗汉的这场法会上,有位自称来自罽宾的外国道人,从其神异表现来看,当为前来应供的罗汉。可见,当时的中土信众相信,通过特定的仪式可以感召西域五百罗汉(可能是其中的一位)前来应供。他们以胡僧的形貌悄悄出现在法会中,一旦被认出便消失不见。宝唱曾撰《饭圣僧法》五卷19,已佚,就此推测,很可能就是供请阿耨达池五百罗汉和罽宾国五百罗汉的仪式文本。
另外,6世纪初中土求法僧在乌场国(印度北部边境山国乌仗那国)也见到了五百罗汉的遗迹。北魏神龟二年(519),西行取经的僧人惠生和宋云到了乌场国,在王城西南五百里的善持山中见到“有昔五百罗汉床,南北两行,相向坐处,其次第相对”20。
通过对6世纪以前中土译经及撰述中有关西域五百罗汉记载的考察和梳理,可以发现:第一,中土有对西域五百罗汉(阿耨达池五百罗汉和罽宾国五百罗汉)的供养法会和仪式文本;第二,信徒可以感遇或者得见罗汉,他们往往化作凡僧与信众打交道(赴斋);第三,此时出现的五百罗汉皆为外国人的身份,并居住在西域。无论是五百罗汉的外国人身份,还是他们远在千万里之外的居所,都不能充分满足中土信众的信仰心理和宗教情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本土化的五百罗汉信仰很快便开始出现,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为这外来的五百罗汉在中土“安家”。
五百罗汉在中土的居所,最著名者乃天台山。学者多认为天台山作为五百罗汉居所的确立是五代以后的事,但是我们以为,这个时间很可能要提前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天台山为圣人居所之说早已有之,东晋孙绰(314-371)《游天台山赋》将天台山与蓬莱相比:“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21李丰楙认为,西方系的昆仑山神话与东方系的蓬莱山神话开始只是各自独立发展,后来依据东西方位的对称逐渐构成神话舆图上神圣空间的对称,由于东方系的蓬瀛在影响上相对弱势,加之东晋政权南移,“滨海地域”的东方圣山出现多位且“一时之间显得游移不定”22,这正是江南地区天台山兴起的背景以及常与蓬莱山相提并论的深层原因。《赵郡王高睿修寺碑》首句即言:“珠林璇室,现昆仑之中;银阙金宫,跱蓬莱之上。”可见李氏所言甚是,这种东西对称的神圣空间格局已成为中土信仰世界的共识。
孙绰文中还说天台山同时为佛道圣者所居:“王乔控鹤以冲天,应真飞锡以蹑虚。”23王乔,即王子乔,为道教中的仙人,《后汉书》卷二十八下《冯衍传》“庶几乎松乔之福”条注引《列仙传》:“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之间,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遂仙去也。”24关于王子乔的信仰地理为何从洛阳附近迁移到了会稽的天台山,魏斌称其为“神仙侨民”的南渡叙事,可能主要是在永嘉乱后流民南迁的背景下出现的。25应真,即罗汉的另一种译名。罗汉这一概念最早输入中国时就被理解为能够飞升幻化的神仙,东汉时出现的《四十二章经》对罗汉的解释就是“能飞行变化,住寿命,动天地”26。伴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出现了一类受佛嘱咐、不入涅槃的住世(寿)罗汉,这种主张很快与中国传统的神仙信仰相结合,为向来喜欢追求长生不死的中国人所接受。“东晋南朝时期天台山神仙洞府想象的核心,是桐柏真人王子乔的金庭馆和金庭洞宫。”27本文认为,《赵郡王高睿修寺碑》中的“金台”即源于这里的“金庭”,而佛教徒将神仙洞府的主人由神仙真人替换为罗汉声闻,采取的策略正是在东西对称的信仰传统下将昆仑山阿耨达池上金台中的五百罗汉搬迁于此。
天台山为罗汉圣地之说虽早已流行,但五百之数究竟有何凭证?梁代慧皎所撰《高僧传》中记载了东晋太元年间(376-396)僧人竺昙猷度过天台石桥、得遇圣寺神僧的故事,未言圣僧数目。同书还记有竺道潜(286-374)的弟子竺法友,“尝从深受阿毘昙,一宿便诵。深曰:‘经目则讽,见称昔人;若能仁更兴大晋者,必取汝为五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讲说。后立剡县城南台寺焉”。28道潜说法友为五百罗汉之一,考虑到他们活动在天台山附近,而道潜僧团与孙绰也有来往,道潜所说“五百”很可能就是天台山五百罗汉,当时浙东文化圈对于天台山五百罗汉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此外,对月光童子信仰的考察也可以为我们理解东晋南北朝时期天台山作为五百罗汉道场的地位提供新的线索和思路。《赵郡王高叡修佛寺碑》中云:“月光童子戏天台之傍,仁祠浮图绕嵩高之侧。”29魏斌已经注意到月光童子与天台山的关系,但他并未就这一关系对天台山作为五百罗汉圣地的意义进行引申。下面,我们将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论述。
三、月光童子信仰与天台山的圣地化
除了《赵郡王高叡修寺碑》外,至迟6世纪初已出现的伪经《首罗比丘见五百仙人并见月光童子经》中已有月光童子活动于天台山的记载:“首罗问大仙曰:‘月光出世当用何时?’‘古月末后,时出境阳,普告诸贤者:天台山引路游观,至介斧山,又到闵子窟列鲁簿:一号太山,二号真君,三号缕练郡圣。’”30将这段经文与疑为寇谦之(365-448)所撰《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相比较:
天尊言:我在宫中观万民,作善者少,兴恶者多。大劫欲末,天尊遣八部监察,以甲申年正月十五日诣太山主簿,共算世间名籍。有修福建斋者,三阳地男女八百人得道,北方魏都地千三百人得道,秦川汉地三百五十人得道,长安晋地男女二百八十七人得道。31
明显可见《首罗比丘经》受到道教“定录成仙”思想的影响。《初学记》卷五《地部上·嵩高山》引卢元明《嵩山记》:“月光童子常在天台,亦来于此。”32前述道教真人王子乔的信仰地理由嵩山移到天台山,而这里月光童子的活动空间也常在两地往来,月光童子的这一特征或许受到了王子乔故事的启发和影响。姜望来指出,东西政权对峙格局形成后,高氏与宇文氏分别采取重佛和重道的宗教政策,北朝道教发展重心由东而西,华岳取代嵩岳成为北朝后期北方道教中心,卢元明(大致活动于北魏末东魏初)撰写《嵩山记》正值道教在佛教进攻下退出嵩岳之时,月光童子由天台山往来于嵩山正是佛教占领嵩岳的写照。33罗汉居所的东迁与道教重心的西移,月光童子的北上与道教神仙的南下,这种相悖与冲突想来绝非偶然,正是两教在传播过程中争夺地域与信众的反映,而分裂变化的政治背景和人口流动的社会环境又在其中起到了牵引推动的作用。
再回到《首罗比丘经》,首罗说五百仙人“烦恼永尽”,且君子国王及大臣“倾心西望而不可止:‘西国真人修何功德,得值入善?作何善业,得见月光出世?而我国人远而不见?’”34五百仙人为“烦恼永尽”的“真人”,足见他们即五百罗汉,而“西望”“西国”又说明他们是西来者,即西域五百罗汉。南岳大师慧思(515-577)立誓愿文中有“自非神仙,不得久住”“为护法故求长命”“作长寿仙见弥勒”35,可见他认为那些住世(寿)护法以待弥勒出世的罗汉即神仙、长寿仙。将长寿神仙与住世罗汉相提并论、等而视之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普遍认识,因此这一时期中土造作的《首罗比丘经》将五百罗汉称为五百仙人也就不足为奇,何况该经本就受到道教成仙思想的影响。《首罗比丘经》说西国五百仙人(即西域五百罗汉)得见月光童子出世,而月光童子与五百罗汉的关系则源于月光童子与弥勒在神格上的同质性。杨惠南就曾指出,月光童子与弥勒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二者在中国政治史上几乎合二为一。36
弥勒信仰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极为兴盛,且有两点鲜明特征;一是弥勒信仰与住世罗汉紧密相关,住世罗汉往往扮演弥勒使者的角色;二是关于弥勒净土的方位多认为在西北高空,这又与前述中土信仰舆图中的昆仑山以及五百罗汉的“老家”一致。东晋名僧道安为弥勒信仰者,他曾于弥勒像前立誓,愿生兜率,后遇异僧,道安问其“来生所往处”,异僧“乃以手虚拨天之西北,即见云开,备睹兜率妙胜之报”,该异僧正是“不得入涅槃,住在西域”的“胡道人”宾头卢。37据北凉道泰所译《入大乘论》,“尊者宾头卢、尊者罗睺罗,如是等十六人诸大声闻散在诸渚,于余经中亦说有九十九亿大阿罗汉,皆于佛前取筹护法,住寿于世界”38。曾获赵郡王高叡等北齐懿戚重臣敬奉的僧人昙衍,临终时“诵念弥勒佛声气俱尽”,而其“未终之前,有梦见衍朱衣螺发颁垂于背,二童侍之升空而西北高逝。寻而便终,时共以为天道者矣。”39分享了弥勒神格特质的月光童子带领五百仙人活动在天台山,这一信仰的诞生是整合了当时已有信仰资源发展出来的。在中国传统东西神圣空间对称、联动的背景下,天台山作为滨海地域的东方系其地位日益重要,成为佛道两教的共同圣地。因为罗汉与神仙在长寿、住世等方面的相类,佛教在道教神仙洞府叙事之外开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圣寺神僧主题。
四、结论
魏斌指出,道教领域内积累发展的山岳认识和神仙洞府想象,在佛教领域内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为此,“洞天福地—神仙治所”构想是否影响到后来山岳菩萨道场的形成,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40其实,早在山岳菩萨道场形成之前,佛教率先把罗汉的住处从“远方夷狄之洞”41搬迁到中土“圣果福地”42。在中国佛教圣地的构建史上,罗汉道场的确立,其时间要远远早于菩萨道场。虽然唐代五台山和峨眉山作为两大佛教名山已被并称43,可是它们文殊和普贤道场的身份尚未被普遍接受。这在道士徐灵府的《天台山记》中有所体现:“今游人所见者正是北桥也,是罗汉所居之所也,意为即小者,则不知大者复在何处,盖神仙冥隐,非常人所睹。”44罗汉是“小者”,菩萨是“大者”,徐灵府很明确天台山作为罗汉居所的地位,却不知晓菩萨住在何处。一方面,这确实与徐灵府常年活动在天台山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天台山作为罗汉道场之说起源早,流传广,唐代时已经累积成一种社会共识,而文殊菩萨领一万菩萨居住在五台山的观念则刚确立不久,仍需时间积淀与传播。因此,有学者认为“天台山被形塑成五百罗汉居住之地,可能也有和五台山相抗衡的意味”45,这种观点恐怕不能成立。
东晋南北朝时期开创于天台山的中土罗汉山岳道场思想,一直流行于隋唐两宋,且在天台山之外,还有罗汉居于其他名山的传闻。据宋崇宁元年(1102)释有挺撰《五百大阿罗汉洞记》(又名《修圣竹林寺碑》),唐初蜀僧法藏感得灵异,获知嵩山竹林寺是罗汉所居的圣寺。46以竹林命名罗汉圣寺早在唐代道宣笔下就有,《律相感通传》中鼓山竹林寺即是由山神从佛请五百罗汉所住。“竹林”成为与“龙池”(即阿耨达池)相类的一种灵境。47除了竹林寺外,山岳中的罗汉道场还有方广寺之名。宋代道士陈田夫所撰《南岳总胜集》记有梁代僧人希遁在天台山遇到五百罗汉之一的慧海尊者,并在他的指引下得入五百罗汉道场——南岳方广寺的故事48。该书还称,在莲花峰北灵辙源有鬼神为罗汉运粮留下来的车辙道。49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天台山的五百罗汉道场也开始有了方广寺的名字。刘淑芬认为,“天台山方广寺之称可能源自南岳衡山”45。宋元符元年(1098)五百罗汉圣号碑言“天台山南岳车辙灵须方广寺内五百大阿罗汉”50,可见二者确实有关。南岳慧海尊者作为五百罗汉的代表,其名号赫然列在明代僧人紫柏(1543-1603)所撰《礼佛仪式》中51,这又是罗汉信仰在中国化过程中另一个层面的表现了。
除了嵩山、衡山外,峨眉、五台、庐山52以及罗浮山、茅山53等皆有罗汉居住的传闻。当然,这些都没有影响到天台山的地位。宋代之后天台山方广寺成为五百罗汉最著名的道场,与五台山相提并论,影响远播海外,这在日僧成寻的求法日记中可见一斑。54天台山这一在东晋南北朝即作为罗汉道场的佛教圣地终于成为东亚佛教文化圈中的重要地理坐标,只是在东西神圣空间的对称格局之下罗汉们如何借助道教神仙思想而从西域迁来的过程已经淹没无闻,幸得《赵郡王高叡修寺碑》等文献中保留的只言片语,为我们更多地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标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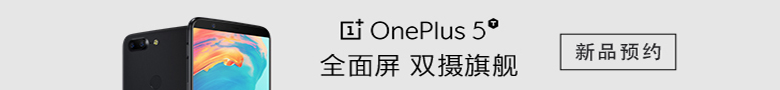
热门推荐